一个屋里有三个燃气表,读数都是零
换了个地方住,从地下室搬到了地面二层,两室一厅的次卧,厕所很近,就在门口,旁边住了两个MM,似乎都是附近医院的护士,熟悉护士MM的人都知道,她们比一般人更加能够忍受脏乱差的环境,我觉得可能是血肉模糊见得太多,已经麻木了,于是我安顿下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洗衣机。南城的天然气管道装了拆,拆了装,一个屋里有三个燃气表,读数都是零,腐败的资本主义。
第一个晚上睡得很不安稳,左脚膝盖疼痛,摸上去似乎有个小包,不像是关节炎的疼痛,但我又未曾在哪里碰撞过,究竟是所为何事呢?窗外就是一只街灯,一直点亮到凌晨。
偶尔回去看看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决定趁着国庆节和勇君的婚礼,去一趟西红市,发现国庆的灰机票怎么都是半价,可能是大家都旅游去了。
小伊问我为什么她生日不送她小礼物,我说不给已婚妇女送礼是我的原则撒你又不是不晓得离婚了就送你小礼物。
地铁十号线空无几人的入口一个黑色衣服黑色长发的MM忧郁的坐在台阶上,我左想右想好像是少了点什么,MAD,没带相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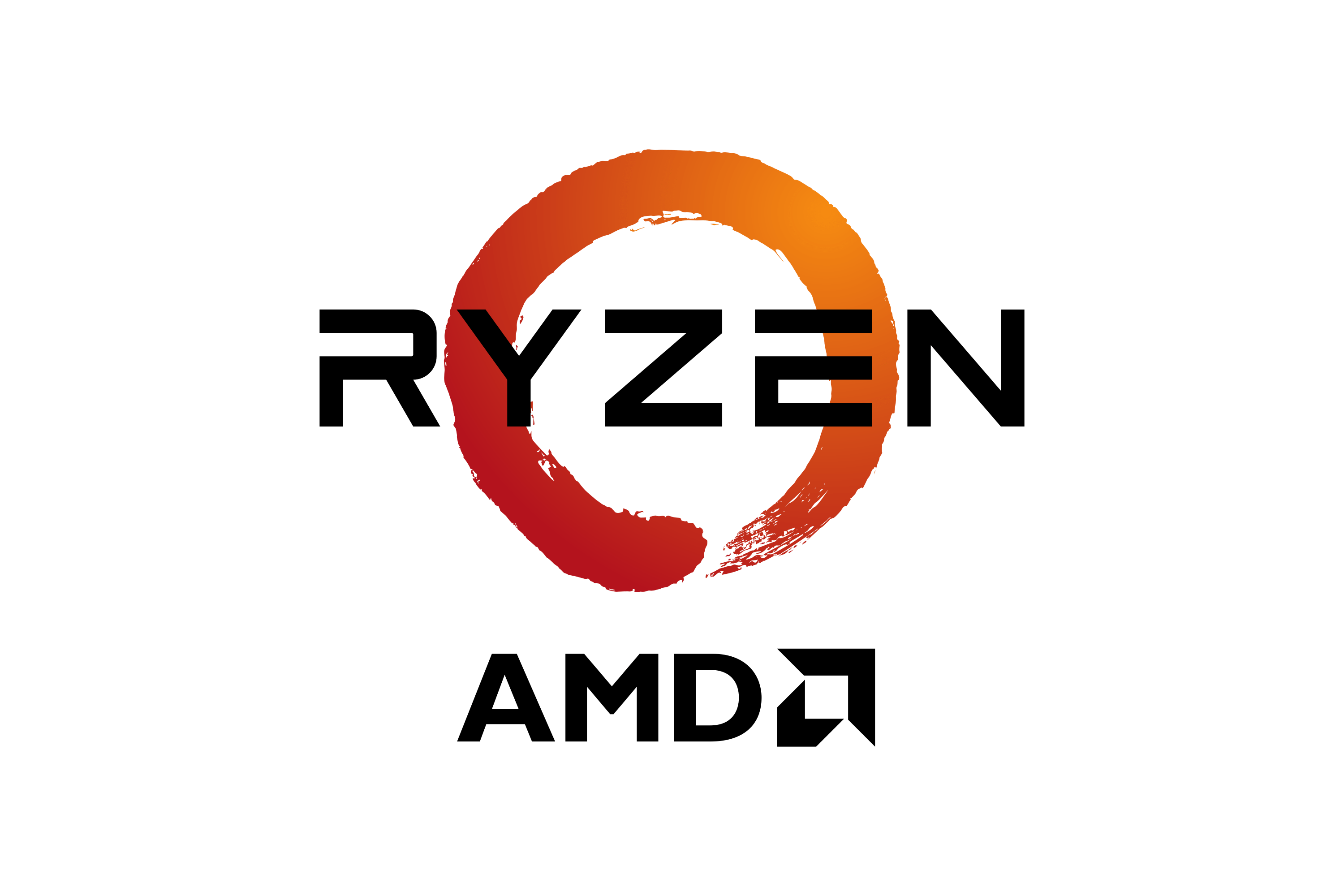
布布
10 月 1 日, 2011 年 @ am 12:49
是搬东西入气。
Ken
10 月 19 日, 2011 年 @ am 10:18
是重复建设好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