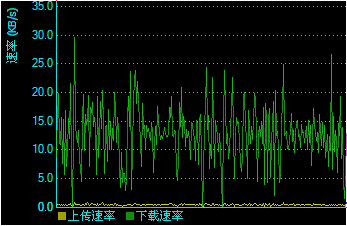一上午我狂吃枸杞,似乎对胃痛有很好的效果,中医讲究胃喜燥不喜寒,就怕整得我肝火旺盛起来……
看起来爽妹在中外合资企业的工作的确如她所说的那样忙碌,因为居然看不到她上网了,想起来同为HR的奥莉维娅姐姐似乎也是经常出差,很少呆在北京,不过像爽妹这样的非资深HR应该不会出差,就算出差她应该也会推掉。
重庆MM又说她得性病了(啊!洁癖!我晕~),我本以为她又和谁谁谁酒后性乱,结果是因为她的检验单上写着HSV阳性,额,这个的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HIV,HPV,不过考虑到她的工作属性,接触的人太多,完全有可能是密切接触传染,但是考虑到她经常酒醉不知归路,到底是怎么传染的估计不可知了。这个HSV完全没有HIV和HPV那么可怕,感觉跟感冒差不多……有很多病,因为没有多大的症状,或者只在特定人群中产生,或者对人寿命的影响不大,医药厂商并不会为这些病研制能有效根治的药物,比如这个HSV,比如延续数千年的肺结核,比如历史不太长久的乙肝,商业社会中的人类维持自身的生存,其实是一个计较投入产出的买卖,生命的过程,更像是一桩生意而已。
——
单纯疱疹病毒(herpes simplex virus 简称HSV)是人类最常见的病原体,人是其唯一的自然宿主。此病毒存在于病人、恢复者或者是健康带菌者的水疱疤液、唾液及粪便中,传播方式主要是直接接触传染,亦可通过被唾液污染的餐具而间接传染。HSV感染现已成为世界上第四大传染病。
HSV主要有两个血清型:HSV-1和HSV-2。HSV-1主要侵犯躯体腰以上部位,可引起口腔、唇、眼、脑及腰以上部位感染,多为隐性感染,并不表现出症状;HSV-2侵及躯体腰以下部位,主要是生殖器,它是引起性病的主要病原体之一。
罹患单纯性疱疹时,病变部位会产生米粒般大小的水泡,发生单一或群集小水泡,通常都是10个左右集结在一起,主要侵犯皮肤及粘膜,会痒痛。水泡周围的皮肤变红,同时会产生轻微的搔痒感和发热。这种水泡若不加以治疗,经过数十日之后,会裂开形成糜烂,然后逐渐痊愈。
HSV的作用机理一般被认为是这样的:首先,HSV病毒寄宿于人体活细胞内,当自我繁殖时,需要利用人体内的DNA聚合酶,依靠人体的蛋白质等为原料进行自我复制,最后出现新的病毒个体后,突破寄主细胞扩散开来,从而使病变范围逐步扩大,病变逐步加重。
HSV单纯疱疹病毒:基因组为双股线性DNA组成,有HSV-1、HSV-2两种血清型,HSV-1型常引起口唇和角膜疱疹;HSV-2型则引起生殖器疱疹,而且主要通过直接接触病灶(性接触)而传播,并导致皮肤病变。HSV病毒有包膜,具有11种包膜糖蛋白,HSV感染细胞后,CPE发展迅速,感染可表现为:原发感染、潜伏再发感染、先天性感染及新生儿感染。常见症状为黏膜或皮肤的局部疱疹。
初次感染 HSV 的时间常不明确 . 第一次出疹后 ,HSV 在神经节内潜伏。 疱疹可被下列因素诱发:过度曝晒阳光 , 发热性疾病 , 身体劳累或情绪紧张以及免疫抑制 . 其诱发机制不明 . 复发病症一般轻于原发病症 .
一旦病毒进入人体,人体能够产生抵抗该病毒的抗体。抗体存在于血流中,对于人体的自然防御(免疫反应)非常重要。在疱疹初次发作后的数周内,抗体可持续产生。
对于生殖器疱疹而言,抗体有助于使得复发症状比初发时更轻微。有趣的是,在从来没有生殖器疱疹发作病史的人中,从其血液检出抗体的情况很常见。在这些人中,有可能是疱疹发作如此轻微以致患者未能觉察到疱疹的发生,或者是这种发作被诊断为其它疾病,或者发作完全无症状而因此未被识别。
生殖器疱疹感染发生在与患有活动性疱疹的性伴的性接触之时,此时生殖器暴露在了病毒中,无论是生殖器性交还是口交均可引起。
初次发作被称为初发或原发感染。在这一阶段,一些病毒进入到了神经节。随后的发作被称为复发,发生在病毒在神经节中复制之时,释放的病毒颗粒沿神经纤维回到初发感染部位。
在女性中,最常受感染的生殖器部位是外阴和阴道入口处,有时疱疹也发生于宫颈。在男性中,疱疹最常见于龟头(阴茎末端)、包皮和阴茎干,有时也发生于睾丸。少数情况下,疱疹可发生男性和女性的肛周、臀部和股部上段。
——